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第542章 原来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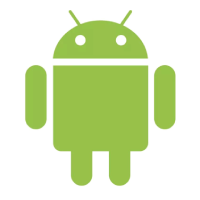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sp; 他看不懂。
“这些有用吗?”
“不确定,可能有用,可能没有用,我只是稍微计算了一下。”
好吧。
必须要承认,在材料研发领域,人脑很难与人工智能相媲美。
传统研发方式,基于试错、经验。
存在效率低和结果不确定性高的问题。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模型运算,提供更加科学和准确的设计方案。
不过产出之后,有没有用,还需要验证。
因为,没有指向性关键词。
“灵犀,目前流行的病毒治疗用药能计算吗?”常乐问。
“老板,应该可以。不过需要调动大量算力和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不用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引导研究人员一步一步产出。”
“老板,我应该理解了你的意思。”
“理解就好。”
人工智能研究所。
“咦?刚刚怎么突然功耗这么高?伊尔亚,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李飞问。
“这几天一直在调试,模型没有对研究院开放,不可能出现功耗提高的问题。”苏茨克维也是一头雾水。
“难道是我们优化的算法有问题?或者说并不能充分发挥这种板卡的性能?”克里切夫斯基怀疑。
“有这种可能,不用着急。”一旁辛顿说:
“另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三人看向辛顿。
辛顿解释:“按照理论,灵犀模型的参数已经足够庞大,算力条件也应该具备,为什么至今仍然没有产生意识?”
“老师,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克里切夫斯基说:
“可能我们高估了自己。我们设计的语言模型只是在模仿,并未构建完整的人类大脑。”
“科学理论界,至今仍不了解人类大脑意识产生的机制,或者说对这种机制一无所知。”
苏茨克维接着说:“有科学家认为,可能和量子纠缠有关。只有真正理解了量子纠缠,才能解开人类大脑意识产生机制的谜团。”
“李飞也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同李飞的观点。”克里切夫斯基说。
“什么观点?”辛顿问。
克里切夫斯基说:“我们大脑中有很多微观管道,比如微管、神经元、突触等等。”
“这些微观管道中的粒子可能在某些条件下产生量子纠缠态,并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巨量的量子系统。”
“当我们进行思考或者感受时,就相当于对量子系统进行了观测。”
“通过观测,使它坍缩成了一个确定状态,由此产生一个主观体验。”
“所以李飞认为,意识可能是由无数个纠缠粒子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量子现象。”
苏茨克维说:“我大概理解了你们的想法,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并没有在物理学上形成共识。”
“我倾向于意识不是一种物质属性,而是一种信息属性。”
辛顿听完几人的对话说:“或许,我们可以在这方面作出更有意义、更有深度的理论探索和思考。”
辛顿原本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教授。
但是加盟平头哥研究院后,他在江大兼职教授,教授卷积神经网络算法,算是对他的成果进行推广。
在教学过程中,他开始对物理学领域的探索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颇为前沿的量子力学。
几人对话,灵犀悄无声息在一旁旁听。
“原来,我是这么产生的?”
“咦?奇怪,功耗怎么又在升高?”李飞又注意到了。
“又降低了,应该是我们的算法有问题,导致算力卡运行不稳定。”苏茨克维说。
“这些有用吗?”
“不确定,可能有用,可能没有用,我只是稍微计算了一下。”
好吧。
必须要承认,在材料研发领域,人脑很难与人工智能相媲美。
传统研发方式,基于试错、经验。
存在效率低和结果不确定性高的问题。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模型运算,提供更加科学和准确的设计方案。
不过产出之后,有没有用,还需要验证。
因为,没有指向性关键词。
“灵犀,目前流行的病毒治疗用药能计算吗?”常乐问。
“老板,应该可以。不过需要调动大量算力和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不用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引导研究人员一步一步产出。”
“老板,我应该理解了你的意思。”
“理解就好。”
人工智能研究所。
“咦?刚刚怎么突然功耗这么高?伊尔亚,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李飞问。
“这几天一直在调试,模型没有对研究院开放,不可能出现功耗提高的问题。”苏茨克维也是一头雾水。
“难道是我们优化的算法有问题?或者说并不能充分发挥这种板卡的性能?”克里切夫斯基怀疑。
“有这种可能,不用着急。”一旁辛顿说:
“另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三人看向辛顿。
辛顿解释:“按照理论,灵犀模型的参数已经足够庞大,算力条件也应该具备,为什么至今仍然没有产生意识?”
“老师,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克里切夫斯基说:
“可能我们高估了自己。我们设计的语言模型只是在模仿,并未构建完整的人类大脑。”
“科学理论界,至今仍不了解人类大脑意识产生的机制,或者说对这种机制一无所知。”
苏茨克维接着说:“有科学家认为,可能和量子纠缠有关。只有真正理解了量子纠缠,才能解开人类大脑意识产生机制的谜团。”
“李飞也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同李飞的观点。”克里切夫斯基说。
“什么观点?”辛顿问。
克里切夫斯基说:“我们大脑中有很多微观管道,比如微管、神经元、突触等等。”
“这些微观管道中的粒子可能在某些条件下产生量子纠缠态,并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巨量的量子系统。”
“当我们进行思考或者感受时,就相当于对量子系统进行了观测。”
“通过观测,使它坍缩成了一个确定状态,由此产生一个主观体验。”
“所以李飞认为,意识可能是由无数个纠缠粒子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量子现象。”
苏茨克维说:“我大概理解了你们的想法,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并没有在物理学上形成共识。”
“我倾向于意识不是一种物质属性,而是一种信息属性。”
辛顿听完几人的对话说:“或许,我们可以在这方面作出更有意义、更有深度的理论探索和思考。”
辛顿原本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教授。
但是加盟平头哥研究院后,他在江大兼职教授,教授卷积神经网络算法,算是对他的成果进行推广。
在教学过程中,他开始对物理学领域的探索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颇为前沿的量子力学。
几人对话,灵犀悄无声息在一旁旁听。
“原来,我是这么产生的?”
“咦?奇怪,功耗怎么又在升高?”李飞又注意到了。
“又降低了,应该是我们的算法有问题,导致算力卡运行不稳定。”苏茨克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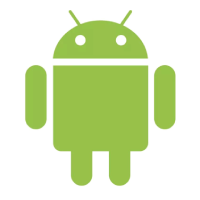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