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第100章 敦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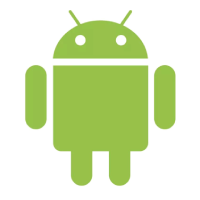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何为世界学术?在苏亦同学看来,在敦煌学兴起的年代,应该就是西方汉学。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此时的敦煌学已经不分东西方之学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显学。是值得我一生研究的学说。”
顿时,众人鼓掌。
现在,老先生的治学态度更值得众人敬佩,然而,谁也没有看不起苏亦的意思,因为苏亦是在场众人唯一可以跟老先生平等对话的存在,仅仅是这点就足够让他们仰望了。
王永兴也对苏亦没有任何偏见,他说,“看待任何问题一定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下,如果脱离了历史,孤立地来看问题,势必有些片面,甚至错误。对于陈寅恪先生来说,他提出来的预流说,也是有时代限制的的,这也跟陈先生的求学经历有关。”
“陈先生的这一预流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其个人学术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的学术语境和学术风气孕育生发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方汉学的影响,陈先生受西洋东方学、汉学以及广义的语言文字学影响甚深。陈先生在留德期间已与西方汉学结缘,受到西方汉学的基本方法———语文考证学的浸润熏陶。正如后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陈先生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日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
“那是因为陈先生1923年他已意识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1927—1932年间,他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西方汉学家的看家本领语文考据法成为陈先生擅用的长技。在执教清华之前,陈先生已大量购置西方学者所着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他回国后任教清华之初,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他所在的清华研究院要求教授讲师必备的三种资格之一就是,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这才有陈先生强调: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
说着,王永兴望着台下苏亦众人,说,“诸位都是我国未来史学之栋梁,如若对敦煌学感兴趣,只当自此立志于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希望诸位他日都能成为敦煌学之预流。”
瞬间,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想起来。
王永兴授课很有感染力。
因为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调动学生情绪的能力,一举一动之间,都能够跟台下起到一种互动。
甚至,言语之间还让苏亦有一种共鸣感。
这就相当难得了。
虽然他的授课,跟其他老师差不多,都是从概念讲起来,然后,他比其他先生更加具有激情。
同样,因为是陈门弟子,他接触的就是最为正统的史学训练,师出名门,他比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更早的接触敦煌学。
所以,他授课的方式,并非是从枯燥的敦煌经卷开始,而是开始讲述学术史。
就是开始跟大家讲述,敦煌学的由来以及敦煌学的发展。
顺带,跟大家讲授一下敦煌学术史。
不过王永兴先生的学术史,更多是放在陈寅恪先生的身上,在推介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他似乎比周一良先生更加直给。
不过因为考古学术史就是前世苏亦读研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内容,苏亦基本上都不陌生。
比如,王永兴提到的敦煌藏经洞经卷流失历史。
除了提到大家熟悉的斯坦因、伯希和之外,还提到日本和尚大谷光瑞的探险队,甚至,还提到俄国的奥登保。
因为这些人都跟敦煌经卷以及壁画的流散在海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部分人都知道斯坦因跟伯希和是直接从道士王圆箓的手中购买大量经卷,实际上,日本人也到了敦煌。
大谷光瑞探险队之中的吉川小一郎跟橘瑞超两人也到了敦煌。
比如吉川,他就取得了莫高窟26方精美的壁画和两尊做工精美的佛像。
不过他到敦煌的时候,藏经洞已成空洞,大部分经卷被晚清政府命敦煌知县运往北京了。
“王圆箓早已将认为有价值的经卷藏在了转经筒里面,并陆续卖给这些外国探险队员们。对外国人已经司空见惯的王道士,看到日本人的到来并不觉得惊讶,于是,吉川小一郎就以11两银元的价格换取了一批唐朝经卷。”
“收到吉川消息的橘瑞超赶到敦煌与之汇合。俩人又从王道生手中各自获得了大量经卷。吉川小一郞在追述王道士给他搬运文书时描述说:态度恰像贼运赃物一样。其中吉川一百多卷,橘瑞超两百六十多卷。最终所获物品用了一百头骆驼才运出敦煌。”
等王永兴提到日本人从王道士手中盗卖敦煌经卷的时候,台下的学生愤怒不已。
这种愤怒比听到斯坦因跟伯希和两人的故事的时候,还来得更加猛烈。
不用想也知道跟两国之间的关系有关系了。
然而,真正对敦煌文物造成大量遗失的人,并非是日本人,而恰恰就是上面的斯坦因跟伯希和。
尤其是伯希和,他比斯坦因这个探险家更加的识货。因为他就是一个语言天才,掌握着多种东方语言,也被誉为杰出的东方学者。
他从敦煌藏经洞挑选经书的方式还跟斯坦因不一样,他是有挑选标准的。
“普通的汉字经卷不要,必须要两面都有文字,如果图文并存的话更好;而且专挑少见的世俗文书,那些双面有文字的世俗文书其实是考古价值最大的社会经济文书(籍账文书、契约文书)和史地文书等等。这种甄选方法的确取走了斯坦因所遗的所有艺术品和藏经洞内的文献精华,使巴黎所存文书在价值上远远高于伦敦藏卷。”
相比较之下斯坦因就弱爆了。
因为这家伙尽量挑选整齐而又漂亮的文书,学术价值如何不管,他看不懂。
提到这里的时候,王永兴痛心疾首。
因为别人不清楚,苏亦再清楚不过,王永兴对敦煌学研究最为擅长的地方就是在敦煌文书。
不过国内学者之所以重视敦煌学,也跟伯希和有关。
1908年伯希和离开敦煌前往北京,第二年的北京宴会上,伯希和将其随身携带的敦煌写本公之于众,顿时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当时罗振玉跟王国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些经卷的价值,呼吁清政府加以保护。
因为罗振玉的个人威望,他们的呼吁起到作用了。
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毛庆蕃,“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省城)。”
然而,学部的本意是好的,还给了六千白银用于购买经卷。
结果执行的时候,就有些蛋疼了。
六千白银直接被县令私吞,散落在外面的经卷一卷都没买,不仅如此,王道士藏起来的经卷也没人管。导致大量藏文卷子、夹板贝叶写经、绢画文献散落民间。
“前往敦煌的1911-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年斯坦因,1914-1915年的奥登堡,都从王道士那里买到数百件敦煌写卷和一些绢画以及从当地收集了大量残卷。”
“不仅如此,运送到京城的藏经洞材料在途中和进京后又经人为截胡了,有价值的经卷被调走,而将普通佛典弄成好几份滥竽充数。这也是为何如今北京图书馆藏卷宗多为一件写经断为十五、六截的残状。这种本世纪早期人为造成的经卷残缺不全的情形导致了藏经洞的文献至今无法全部复原,仍然散落在世界各地。”
听到这话,苏亦突然想起来,在莫高窟三清宫前那句陈寅恪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其实这句话也是出自陈寅恪1930年给陈垣《敦煌劫余录》作的序,原话是“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陈寅恪的本意是引用这句别人说的话,对当时学界基于这一论断的一些倾向加以批判。大多数人对这句话的认识,以至把它刻在莫高窟石头上的做法,都与陈寅恪的本意南辕北辙。
但不管如何,敦煌文物流失在世界各地,确实一段伤心史。
“而敦煌学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根源在于敦煌宝藏发现后,其文献和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大批收集品集中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西方学者得以先行研究发表。敦煌学实际上兴起于国外,其中,法国汉学家起步最早,且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以沙畹、伯希和、马伯乐为代表。1909年,因为伯希和在敦煌所获宝藏,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敦煌学初兴之际,国外汉学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成果之丰,足令国内学者汗颜。”
“当然,国内学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早在民国时期,国内的学者一直试图把汉学中心从巴黎还有东京变成北平。这点,咱们苏亦同学在新生见面上有做过发言,我就不赘述了。”
果然,王永兴对苏亦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讲课的时候,还不忘了引用他的观点。
一下子,众人的目光又再次落在苏亦的身上,使得他再一次成为阶梯教室里面最靓的崽。
顿时,众人鼓掌。
现在,老先生的治学态度更值得众人敬佩,然而,谁也没有看不起苏亦的意思,因为苏亦是在场众人唯一可以跟老先生平等对话的存在,仅仅是这点就足够让他们仰望了。
王永兴也对苏亦没有任何偏见,他说,“看待任何问题一定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下,如果脱离了历史,孤立地来看问题,势必有些片面,甚至错误。对于陈寅恪先生来说,他提出来的预流说,也是有时代限制的的,这也跟陈先生的求学经历有关。”
“陈先生的这一预流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其个人学术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的学术语境和学术风气孕育生发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方汉学的影响,陈先生受西洋东方学、汉学以及广义的语言文字学影响甚深。陈先生在留德期间已与西方汉学结缘,受到西方汉学的基本方法———语文考证学的浸润熏陶。正如后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陈先生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日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
“那是因为陈先生1923年他已意识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1927—1932年间,他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西方汉学家的看家本领语文考据法成为陈先生擅用的长技。在执教清华之前,陈先生已大量购置西方学者所着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他回国后任教清华之初,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他所在的清华研究院要求教授讲师必备的三种资格之一就是,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这才有陈先生强调: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
说着,王永兴望着台下苏亦众人,说,“诸位都是我国未来史学之栋梁,如若对敦煌学感兴趣,只当自此立志于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希望诸位他日都能成为敦煌学之预流。”
瞬间,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想起来。
王永兴授课很有感染力。
因为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调动学生情绪的能力,一举一动之间,都能够跟台下起到一种互动。
甚至,言语之间还让苏亦有一种共鸣感。
这就相当难得了。
虽然他的授课,跟其他老师差不多,都是从概念讲起来,然后,他比其他先生更加具有激情。
同样,因为是陈门弟子,他接触的就是最为正统的史学训练,师出名门,他比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更早的接触敦煌学。
所以,他授课的方式,并非是从枯燥的敦煌经卷开始,而是开始讲述学术史。
就是开始跟大家讲述,敦煌学的由来以及敦煌学的发展。
顺带,跟大家讲授一下敦煌学术史。
不过王永兴先生的学术史,更多是放在陈寅恪先生的身上,在推介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他似乎比周一良先生更加直给。
不过因为考古学术史就是前世苏亦读研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内容,苏亦基本上都不陌生。
比如,王永兴提到的敦煌藏经洞经卷流失历史。
除了提到大家熟悉的斯坦因、伯希和之外,还提到日本和尚大谷光瑞的探险队,甚至,还提到俄国的奥登保。
因为这些人都跟敦煌经卷以及壁画的流散在海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部分人都知道斯坦因跟伯希和是直接从道士王圆箓的手中购买大量经卷,实际上,日本人也到了敦煌。
大谷光瑞探险队之中的吉川小一郎跟橘瑞超两人也到了敦煌。
比如吉川,他就取得了莫高窟26方精美的壁画和两尊做工精美的佛像。
不过他到敦煌的时候,藏经洞已成空洞,大部分经卷被晚清政府命敦煌知县运往北京了。
“王圆箓早已将认为有价值的经卷藏在了转经筒里面,并陆续卖给这些外国探险队员们。对外国人已经司空见惯的王道士,看到日本人的到来并不觉得惊讶,于是,吉川小一郎就以11两银元的价格换取了一批唐朝经卷。”
“收到吉川消息的橘瑞超赶到敦煌与之汇合。俩人又从王道生手中各自获得了大量经卷。吉川小一郞在追述王道士给他搬运文书时描述说:态度恰像贼运赃物一样。其中吉川一百多卷,橘瑞超两百六十多卷。最终所获物品用了一百头骆驼才运出敦煌。”
等王永兴提到日本人从王道士手中盗卖敦煌经卷的时候,台下的学生愤怒不已。
这种愤怒比听到斯坦因跟伯希和两人的故事的时候,还来得更加猛烈。
不用想也知道跟两国之间的关系有关系了。
然而,真正对敦煌文物造成大量遗失的人,并非是日本人,而恰恰就是上面的斯坦因跟伯希和。
尤其是伯希和,他比斯坦因这个探险家更加的识货。因为他就是一个语言天才,掌握着多种东方语言,也被誉为杰出的东方学者。
他从敦煌藏经洞挑选经书的方式还跟斯坦因不一样,他是有挑选标准的。
“普通的汉字经卷不要,必须要两面都有文字,如果图文并存的话更好;而且专挑少见的世俗文书,那些双面有文字的世俗文书其实是考古价值最大的社会经济文书(籍账文书、契约文书)和史地文书等等。这种甄选方法的确取走了斯坦因所遗的所有艺术品和藏经洞内的文献精华,使巴黎所存文书在价值上远远高于伦敦藏卷。”
相比较之下斯坦因就弱爆了。
因为这家伙尽量挑选整齐而又漂亮的文书,学术价值如何不管,他看不懂。
提到这里的时候,王永兴痛心疾首。
因为别人不清楚,苏亦再清楚不过,王永兴对敦煌学研究最为擅长的地方就是在敦煌文书。
不过国内学者之所以重视敦煌学,也跟伯希和有关。
1908年伯希和离开敦煌前往北京,第二年的北京宴会上,伯希和将其随身携带的敦煌写本公之于众,顿时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当时罗振玉跟王国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些经卷的价值,呼吁清政府加以保护。
因为罗振玉的个人威望,他们的呼吁起到作用了。
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毛庆蕃,“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省城)。”
然而,学部的本意是好的,还给了六千白银用于购买经卷。
结果执行的时候,就有些蛋疼了。
六千白银直接被县令私吞,散落在外面的经卷一卷都没买,不仅如此,王道士藏起来的经卷也没人管。导致大量藏文卷子、夹板贝叶写经、绢画文献散落民间。
“前往敦煌的1911-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年斯坦因,1914-1915年的奥登堡,都从王道士那里买到数百件敦煌写卷和一些绢画以及从当地收集了大量残卷。”
“不仅如此,运送到京城的藏经洞材料在途中和进京后又经人为截胡了,有价值的经卷被调走,而将普通佛典弄成好几份滥竽充数。这也是为何如今北京图书馆藏卷宗多为一件写经断为十五、六截的残状。这种本世纪早期人为造成的经卷残缺不全的情形导致了藏经洞的文献至今无法全部复原,仍然散落在世界各地。”
听到这话,苏亦突然想起来,在莫高窟三清宫前那句陈寅恪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其实这句话也是出自陈寅恪1930年给陈垣《敦煌劫余录》作的序,原话是“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陈寅恪的本意是引用这句别人说的话,对当时学界基于这一论断的一些倾向加以批判。大多数人对这句话的认识,以至把它刻在莫高窟石头上的做法,都与陈寅恪的本意南辕北辙。
但不管如何,敦煌文物流失在世界各地,确实一段伤心史。
“而敦煌学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根源在于敦煌宝藏发现后,其文献和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大批收集品集中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西方学者得以先行研究发表。敦煌学实际上兴起于国外,其中,法国汉学家起步最早,且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以沙畹、伯希和、马伯乐为代表。1909年,因为伯希和在敦煌所获宝藏,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敦煌学初兴之际,国外汉学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成果之丰,足令国内学者汗颜。”
“当然,国内学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早在民国时期,国内的学者一直试图把汉学中心从巴黎还有东京变成北平。这点,咱们苏亦同学在新生见面上有做过发言,我就不赘述了。”
果然,王永兴对苏亦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讲课的时候,还不忘了引用他的观点。
一下子,众人的目光又再次落在苏亦的身上,使得他再一次成为阶梯教室里面最靓的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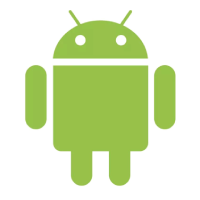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