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第95章 唐代密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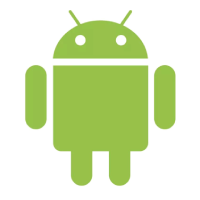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因此能够完成翻译本身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前世的时候,苏亦曾经读过译本,然后就顺势找了原版的论文。
可以说,周一良是苏亦最为感兴趣的北大历史系教授之一。
甚至,苏亦对于他的兴趣比恭三先生还要大。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个人偏爱佛教考古而非宋史研究的原因。
钱文忠的译本,按照苏亦的能力来说,是没有办法挑错的。
更为难得的是,通过全文的校读明显可能发现越到后面,译者的错误越少。
像前面出现的不少问题,如回译等,到了后面都有了非常精细的处理。像沙畹等大师的很多古着法译,在汉译中都作了精确的定位与回译。
这也反应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即翻译本身对于译者也是一个有益的学习过程。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的翻译,只是错多错少而已,所以对于任何真诚的学术翻译我们都应该鼓励。
而且翻译全书并非易事,不过,苏亦在翻看译本的时候,确实遇到不少读着不太通顺或者说存疑的地方。
如果没有译本的话,以苏亦半吊子的英文是很难完全读懂这片论文的。
然而,不管如何,这年头有人愿意去翻译这些偏门的论文已经是很难得了。
所以,也不需要苛求什么。
再说当年苏亦也不是研究这个领域,只不过,这个时候,突然遇到周一良先生,苏亦就觉得不应该错过这个请教的机会了。
不然,天知道要等多久才有这样的机会遇到周先生,并且,还能够跟对方搭上话。
听到苏亦的话,周一良望着他一眼以后,就示意他拿上书本,“咱们出去聊,不要在这里耽搁其他同学借书。”
除了二楼借阅室,周一良望着苏亦,“你就是苏亦同学吧?宿白先生学生?”
“周先生,认识我?”
苏亦惊讶,自己那么出名了吗?
这位连讲台都没有再出现的老人,竟然能够知道自己的名字?
周一良点头,“虽然未曾见过,但你的名字我确实已经多次听说过了,观你年纪,还有你手中的借书证,便可猜测你的身份。从你进入历史系复试的时候,咱们系里面关于你的讨论就不少,同样,前段时间你们王永兴教授去我住处拜访我的时候,曾经谈论过你,还曾经说恭三先生想要收你为徒,却被你拒绝了。”
得,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这个的小八卦,在北大历史系,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不,连这位老爷子也知道了。
而且,周一良提到的王永兴,这位也是一个大名人。
王永兴,着名的历史学家,在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时候曾经跟随过陈寅恪先生学习,是陈门众多弟子之中,成就比较高的几位之一。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篯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篯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
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这话是因为陈当初在拒绝郭老以及李仲揆副院长提议其任职中科院历史所第二所长的时候所说的。
尤其是陈先生说他读过《资本论》,关于这事还有一个轶事,就是有人说陈先生不懂马列主义,然后就被噼里啪啦的打脸了。
然而,这个时候,周一良并没有跟陈寅恪决裂,破门之罚并没有发生。
那么陈周两人之间关于“破门之罚”,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桂林,周一良在美国哈佛留学,战火的阻隔,让陈寅恪想起和周一良战前书信往来论学之旧事。
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开端充满感情地写道:“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
由此可见陈周师生情感之深。
然而,特殊年代,周一良受舆论和形势的影响,在家信中将胡适称之为“文化买办”,随后着文《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评判陈。
周一良此举,完全背叛了陈寅恪,并对其反戈一击,师生断谊。
1963年,陈寅恪编订《丛稿》时,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前记录陈周师生之情的序删掉,以示往日师生情谊不再。
这种举动,可以和古代先生对弟子的“破门”视之。
那么破门又是什么呢?
这个这是古代读书人对门下弟子的一种惩罚之道。
历史上,老师将学生逐出师门,即所谓“破门”,这不是小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地君亲师”一说,师生关系并不亚于父子关系,学生之于老师,除求学外尚有尊亲之意。
所以,在古代,被老师逐出师门、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同样为社会伦理所不容。
后来,因为梁晓的缘故,周一良陷入极度的自责之中。
99年,在中大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病在身的周一良不能到会,却向会议提交了《向陈先生请罪》。这篇文章披露了写批陈文章这件鲜为人知的不光彩往事,而且还触及灵魂,做了深深的忏悔。“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至于王永兴,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说到这些有些跑题了。
苏亦跟随着周一良走出图书馆,走在林荫道上,望着这位老人有些佝偻孤独的背影,苏亦忍不住问,“周先生,学生有个疑惑,在您的论文原文页242-3中是:Byapplyingoiltohispalmhewasabletoseewhatwashappeningathou-sandmilesaway。此处的“palm”是贝叶的意思吗?”
前世的时候,苏亦曾经读过译本,然后就顺势找了原版的论文。
可以说,周一良是苏亦最为感兴趣的北大历史系教授之一。
甚至,苏亦对于他的兴趣比恭三先生还要大。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个人偏爱佛教考古而非宋史研究的原因。
钱文忠的译本,按照苏亦的能力来说,是没有办法挑错的。
更为难得的是,通过全文的校读明显可能发现越到后面,译者的错误越少。
像前面出现的不少问题,如回译等,到了后面都有了非常精细的处理。像沙畹等大师的很多古着法译,在汉译中都作了精确的定位与回译。
这也反应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即翻译本身对于译者也是一个有益的学习过程。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的翻译,只是错多错少而已,所以对于任何真诚的学术翻译我们都应该鼓励。
而且翻译全书并非易事,不过,苏亦在翻看译本的时候,确实遇到不少读着不太通顺或者说存疑的地方。
如果没有译本的话,以苏亦半吊子的英文是很难完全读懂这片论文的。
然而,不管如何,这年头有人愿意去翻译这些偏门的论文已经是很难得了。
所以,也不需要苛求什么。
再说当年苏亦也不是研究这个领域,只不过,这个时候,突然遇到周一良先生,苏亦就觉得不应该错过这个请教的机会了。
不然,天知道要等多久才有这样的机会遇到周先生,并且,还能够跟对方搭上话。
听到苏亦的话,周一良望着他一眼以后,就示意他拿上书本,“咱们出去聊,不要在这里耽搁其他同学借书。”
除了二楼借阅室,周一良望着苏亦,“你就是苏亦同学吧?宿白先生学生?”
“周先生,认识我?”
苏亦惊讶,自己那么出名了吗?
这位连讲台都没有再出现的老人,竟然能够知道自己的名字?
周一良点头,“虽然未曾见过,但你的名字我确实已经多次听说过了,观你年纪,还有你手中的借书证,便可猜测你的身份。从你进入历史系复试的时候,咱们系里面关于你的讨论就不少,同样,前段时间你们王永兴教授去我住处拜访我的时候,曾经谈论过你,还曾经说恭三先生想要收你为徒,却被你拒绝了。”
得,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这个的小八卦,在北大历史系,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不,连这位老爷子也知道了。
而且,周一良提到的王永兴,这位也是一个大名人。
王永兴,着名的历史学家,在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时候曾经跟随过陈寅恪先生学习,是陈门众多弟子之中,成就比较高的几位之一。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篯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篯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
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这话是因为陈当初在拒绝郭老以及李仲揆副院长提议其任职中科院历史所第二所长的时候所说的。
尤其是陈先生说他读过《资本论》,关于这事还有一个轶事,就是有人说陈先生不懂马列主义,然后就被噼里啪啦的打脸了。
然而,这个时候,周一良并没有跟陈寅恪决裂,破门之罚并没有发生。
那么陈周两人之间关于“破门之罚”,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桂林,周一良在美国哈佛留学,战火的阻隔,让陈寅恪想起和周一良战前书信往来论学之旧事。
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开端充满感情地写道:“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
由此可见陈周师生情感之深。
然而,特殊年代,周一良受舆论和形势的影响,在家信中将胡适称之为“文化买办”,随后着文《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评判陈。
周一良此举,完全背叛了陈寅恪,并对其反戈一击,师生断谊。
1963年,陈寅恪编订《丛稿》时,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前记录陈周师生之情的序删掉,以示往日师生情谊不再。
这种举动,可以和古代先生对弟子的“破门”视之。
那么破门又是什么呢?
这个这是古代读书人对门下弟子的一种惩罚之道。
历史上,老师将学生逐出师门,即所谓“破门”,这不是小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地君亲师”一说,师生关系并不亚于父子关系,学生之于老师,除求学外尚有尊亲之意。
所以,在古代,被老师逐出师门、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同样为社会伦理所不容。
后来,因为梁晓的缘故,周一良陷入极度的自责之中。
99年,在中大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病在身的周一良不能到会,却向会议提交了《向陈先生请罪》。这篇文章披露了写批陈文章这件鲜为人知的不光彩往事,而且还触及灵魂,做了深深的忏悔。“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至于王永兴,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说到这些有些跑题了。
苏亦跟随着周一良走出图书馆,走在林荫道上,望着这位老人有些佝偻孤独的背影,苏亦忍不住问,“周先生,学生有个疑惑,在您的论文原文页242-3中是:Byapplyingoiltohispalmhewasabletoseewhatwashappeningathou-sandmilesaway。此处的“palm”是贝叶的意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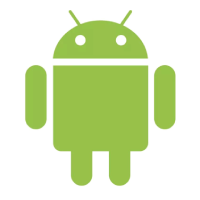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