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第111章 和谈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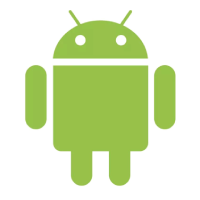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夏代有天神崇拜、祖先崇拜,同时并存的有英雄、自然神、鬼神、谷神崇拜。从《尚书·甘誓》可知,夏启征讨有扈氏就是以天命为合法性依据的,其理由是对方轻蔑神灵,把人的生存秩序和自然环境弄得乱七八糟,即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从甲骨卜辞和《尚书》诸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确知殷代有皇天、上帝、帝或天帝的崇拜与祖先神、自然神崇拜等。从商汤、周公所发布的文告中可知,他们都以天为至上神,以天命为根据,以天与天命为王权所出之本原。西周进一步发展了天、天命、天子的观念,使天神不再是与人们相对立的盲目支配的力量,不仅主宰自然,而且主宰社会,与地上的最高统治者有了亲密的关系,成为周人建立的宗法制度之政治与道德的立法者。天神把疆士臣民委托给天子并时刻监督之,它保佑有德的君主,惩罚胡作非为的统治者。周人不仅把天神理性化了,而且把祖宗神理性化了,在祖宗神灵崇拜中也加强了政治与道德意义,进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观念。[2]天的意志与人的意志可以沟通,这就是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可以了解天的意志,天的意志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小民百姓的意志。宗教、政治、道德结合成一体,尤以道德为枢纽。
夏商周都“以祖配天”,周代尤能把“以祖配天”转化成“以德配天”,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敬慎其德才能祈天永命。统治者必须以临深履薄的态度处理政务,对待民众,否则天命会得而复失。这无疑是人文的觉醒,然而是在宗教神灵崇拜中产生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中透显出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主体性。这种人文或人或主体的觉醒,绝不是寡头的去神化的人文精神与主体性。人总是宗教性的动物。周代关于“天”、“天命”的信仰和敬畏,涉及到人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生存问题,其与人的贯通,始终以道德为枢纽,使得道德理性有了终极依据。孔子说:“畏天命”(《论语?季氏》);“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泰伯》);“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孔子保留了天的神秘性与对天的敬畏,同时把天作为内在道德的根源。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可以说是士君子个体与终极之天相贯通的典型论述,在这里,有终极信仰的人可以安立自己,人可以体知天、上达天德、与天地鼎足而三,人可以让天地人物各遂其性,人在天地中的地位由此而确定。这是中国古代生存哲学的宗纲和大本。
人生存于天地人物我之间,首先生存于天地之间。有关“天”的问题,我们可以分析为自然之天、意志之天、神性意义之天、命运之天、义理(即价值理性)之天等等,但中国古人对于天有一个整全的看法,这主要是西周至孔孟的看法长期浸润的结果。“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夏商周都“以祖配天”,周代尤能把“以祖配天”转化成“以德配天”,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敬慎其德才能祈天永命。统治者必须以临深履薄的态度处理政务,对待民众,否则天命会得而复失。这无疑是人文的觉醒,然而是在宗教神灵崇拜中产生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中透显出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主体性。这种人文或人或主体的觉醒,绝不是寡头的去神化的人文精神与主体性。人总是宗教性的动物。周代关于“天”、“天命”的信仰和敬畏,涉及到人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生存问题,其与人的贯通,始终以道德为枢纽,使得道德理性有了终极依据。孔子说:“畏天命”(《论语?季氏》);“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泰伯》);“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孔子保留了天的神秘性与对天的敬畏,同时把天作为内在道德的根源。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可以说是士君子个体与终极之天相贯通的典型论述,在这里,有终极信仰的人可以安立自己,人可以体知天、上达天德、与天地鼎足而三,人可以让天地人物各遂其性,人在天地中的地位由此而确定。这是中国古代生存哲学的宗纲和大本。
人生存于天地人物我之间,首先生存于天地之间。有关“天”的问题,我们可以分析为自然之天、意志之天、神性意义之天、命运之天、义理(即价值理性)之天等等,但中国古人对于天有一个整全的看法,这主要是西周至孔孟的看法长期浸润的结果。“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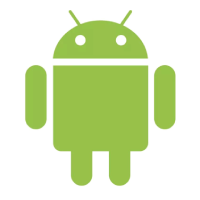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